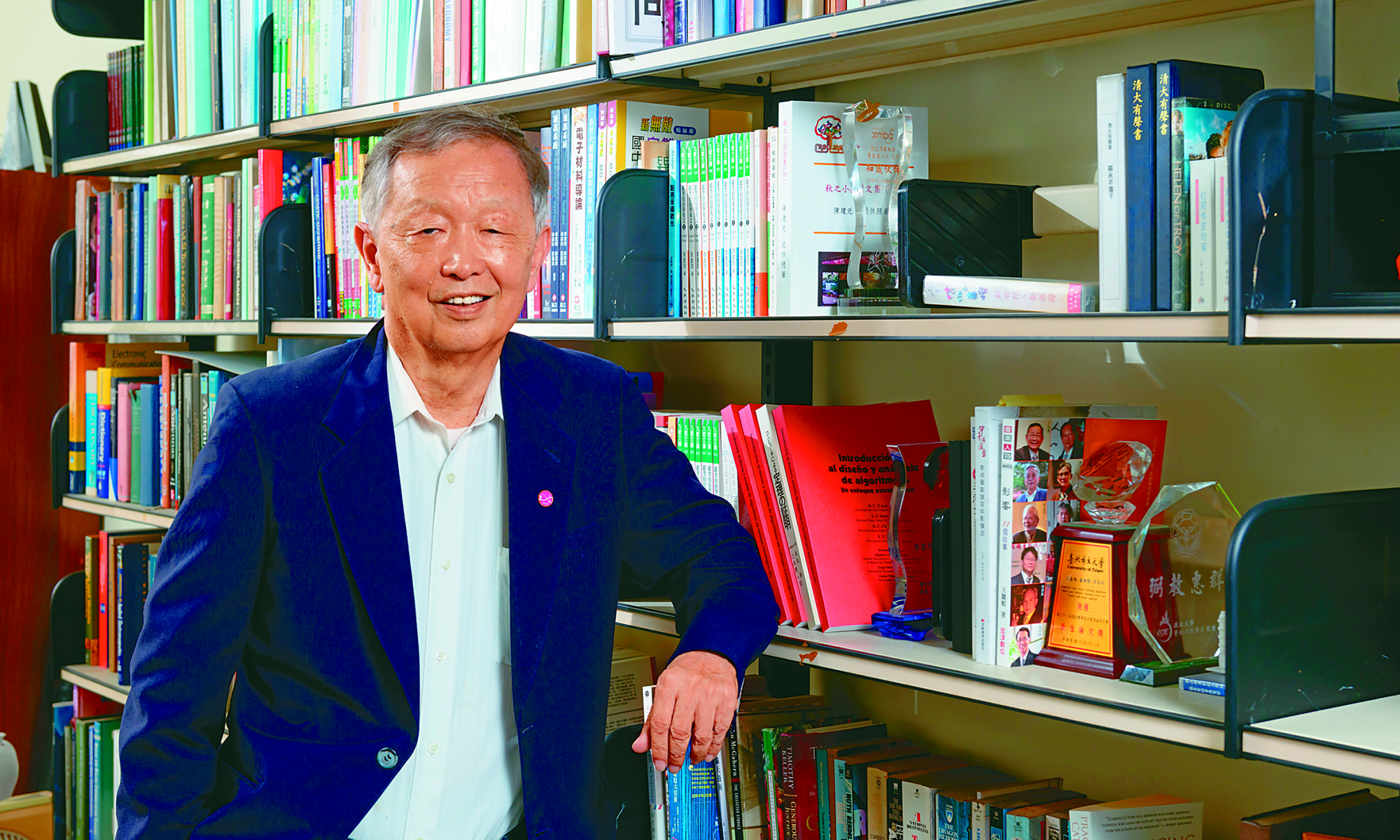我在民國六十四年回國的,屈指算來,已經是三十年了,在這三十年內,我扮演唯一的角色是老師。很多人同樣的工作做了三十年,會感到厭煩,我卻一點也沒有這種感覺,不僅沒有,而且越做越起勁,我常希望上蒼能再給我三十年的時間,好讓我再做三十年的老師。
我最近常接受訪問,幾乎每次訪問,都會被問到一個問題:「李教授,你有沒有發覺現在的學生,跟過去的比起來,是大不如前了?」我知道訪問者的心意,他希望我將我的學生大罵一頓,說他們全是一批只會玩的小子,成天不用功,課也不上,而我當年年輕時,充滿了理想和抱負,熱愛追求真理,也成天想報效國家,因此我們這些老頭子,當年都是熱血青年,當然也用功得不得了。和今日的懶散青年相比,簡直不可比也。
而我每次的回答都令他們大為失望,因為我總是說我現在的學生和當年的我並無顯著的差異,我過去的確比較用功,可是這不是因為我在追求真理,我希望我的成績好,是因為我當時在準備出國留學,總不能功課成績太差也。我那時也比較不會玩,這不是因為我不好玩,而是當時我只有一輛老爺腳踏車,在市內騎騎還可以,騎遠了,保證會出毛病的。現在的學生好像都有機車,當然到了週末,就不知瘋到哪裡去了。
很多教授說現在的學生不用功,這點我最不能同意,我的學生應該算是太用功了。今年暑假,我本來想好好地休息一下的,但我的學生卻要求我教他們符號邏輯,這也不怪他們,畢竟我是這方面的偉大專家也,所以別的教授紛紛到夏威夷去度假之時,我卻在埔里上課,好在埔里的夏天不太熱,我教符號邏輯的教室是一樓的教室,窗外有大樹成蔭,學生除了聽我口沫橫飛的講課以外,還可以聽到窗外的鳥聲,我要是學生,聽到我的精彩講課,一定會覺得如沐春風也。
至於我呢?我已好久沒有教符號邏輯了。令我感到非常高興的是:我對符號邏輯因此有了一種更深的認識。三十年前,我對符號邏輯已有了些瞭解,今年夏天,我重作馮婦,發現我可以用一種新的方式來解釋符號邏輯,我真該感謝我的學生。
每年暑假,都會有新的碩士向我們報到,我本人不太管這些新到的學生,可是他們的學長會替他們安排研究室的位置,以及領取電腦,除此之外,這些可憐的新生立刻要開始念演算法,而且每週都有一次考試,考題由一位有虐待狂的研二學生出,每一位新生都要乖乖地被學長考,大概也敢怒不敢言也。可是,這種作法,的確有用。我們的新生經過暑假以後,就可以開始看論文了,這些論文,都是相當難的。
除了虐待新生以外,我的學生還有一個優良的傳統,那就是每個週末,同學們都要輪流上台去報告他們所看過的論文,只要稍有不慎,資深的學長們就會要求他們重來一次。雖然這些同學被學長們找麻煩,一定氣得半死,但是我的學生的確是受過嚴格磨練的。這種嚴格磨練,對他們的學業極有幫助。
學生必須用功,乃是天經地義的事,我的學生即使在週末,也都留在研究室裡,很少回家的。如果外出回家,我也會追蹤到他,因為他們在報到的那一天,就給了我他們的手機號碼,有一位有幸災樂禍心理的學長,將他們的號碼輸入了我的手機,不僅如此,他們的研究資料也都放在網頁上,如果我在家裡對他們的研究不滿意,哪怕在天涯海角,也可以立刻上網去修改程式。有一次,我的一位寶貝學生在墾丁遊玩,被我追蹤到了以後,花了好幾個小時泡在網咖裡改程式,他後來再也不去墾丁了,怕引起慘痛的回憶也。
我有時會出去演講,每次都央求一位同學開車,一來是因為我懶得找路,二來是回來的時候,一定已經很疲倦了,要再開車會吃不消。每次快回到暨大的時候,那位學生就會用手機通知校內同學,說我們快到了。為什麼如此做呢?因為我前門才離開,學生就從後門溜去籃球場打球去了,早一點通風報訊,使這些小子來得及洗個澡,等我回來的時候,每個人都正襟危坐在書桌之前做用功狀。
學電腦的學生,當然都有電腦,學生們使用電腦,應該是做研究的,可是他們常常在電腦上玩電動遊戲,沒有料到我正好進來,他正玩得起勁,已到了渾然忘我的境界,當然不知後方來了個指導教授。我有一次發現那個小子玩的遊戲中,有一個角色叫做李家同,在武功那一欄裡,填了個「差」。我事後把他罵了一頓,那位同學向我解釋,其實只要假以時日,李家同的武功就會好起來了。我弄不清楚他的說法對不對,但我從此痛恨電玩,認為應該加以禁止,以免像我這種老師,在遊戲中個個都是武功奇差也。
我知道學生一定要英文好,否則將來競爭力一定不夠,但我又認為我不能空講,所以我每週唸一段英文文章給學生聽,錄音以後的文章放在網站上,學生除了要看英文文章以外,批改時也可以錄音批改的過程,所以學生可以事後清清楚楚地看到批改,也聽到批改的解釋,以及我的嘆息聲。所有的學生所犯的錯,我都記錄下來,向同學們解釋。
這還不夠,我還要求全體同學每週向我報告一次他們所學的英文生字,至少十個生字,有些同學每週所學到的生字,有三十個之多,這些生字都鍵入一個Excel檔案,我每週週末都會去看看他們增加了什麼樣的生字。
信不信由你,學生畢業以後,依然要寫中翻英,依然要交英文生字,有些同學會偷懶,我會打電話去罵。我在靜宜大學作校長的時候,有一個小子在校長室工讀,到現在仍然沒有逃脫我的魔掌,每一次的中翻英從不缺席,可是他稍微有點混,每一週一定只有十個生字,不多也不少,哪有這麼巧。這個小子在一個偉大的日商公司工作,公司會招待他們出國旅遊,出國以前他也趕快地把中翻英做好,而且打電話告訴我:「老師,功課做完了,可以出去玩了。」他有一個好朋友,有一天打電話向我問好,也被我抓到做翻譯,交生字,這個學生最認真,生字最多,翻譯也做得非常好。
我一直嚴格地要求學生,學生也因此怕我。有一位非常調皮的學生,有一天晚上在宿舍看電視,一不小心,看到了一個我接受採訪的節目,他當場嚇得一身冷汗,因為他不太用功,常被我罵,這一週他又未做習題,作賊心虛,在夜深人靜的時候,看到了我,猶如看到了鬼一般。
我的學生畢業以後,依然如此,在電視上看到我,或者是在書店裡看到了我的「肖像」,都會心跳加速,他們過去都生活在隨時可能被罵的情況之中,現在已經畢業了,看到我的影子,仍然以為我會罵他們。
我常常想,好的大學,一定是長幼有序的,我過去在清華時,就是如此,現在依然如此。每次上課,學長坐在一邊,學弟妹坐在另外一邊,學弟妹絕對不會跑去和學長們坐在一起。連吃飯時都是如此,坐在我旁邊的永遠都是博士班的學生,才進來的碩一學生,連話都不敢多講。其實這是很自然的事,那些學長們回答問題時,永遠精準而正確,學弟們有時根本不知問的是什麼東西。
我真正全副精神教書,也是最近的事,過去一直擔任行政職務,成天為爭取經費而傷腦筋。現在無官一身輕,終於享受到純教書的樂趣。我不做校長,就沒有司機,幸好有一位電機系教授與我同行,一路上我向他學了不少通訊的課,後來暨大通訊所所長也參加共同開車,兩位通訊專家本來以為我程度太差,常常講些行話來唬我。沒有想到我雖已快是七十老翁,學起來卻快得很,他們只好傾囊相授。對我來講,聽他們授課,真是一大福氣也。
教了通訊,我後來還教類比線路,這就更難了,好在我的同事們都肯教我,電機系有一位傻小子,叫做賴育瑄者,被我纏住了不放。賴育瑄成天被我打電話去騷擾,絲毫不以為意,因為他發現我有一個學生,已經在美國,我仍會寫信去鬧他。賴育瑄是個很認命的人,他常說:「逃也逃不掉的,我即使逃到美國去,李教授也會找到我的。」
教新的課程,使我會有寶刀未老的感覺,每個人到了六十歲,就會擔心自己已經不行了。廉頗老矣,尚能飯否?到目前為止看來,我好像還能吸收新的知識。我們做老師的人,平時最大的快樂當然是和年輕人胡扯,除此之外,一直吸收新知識才是我們的一大樂事,每一週,我都會聽學生研讀論文的心得,通常這永遠是我個人最快樂的時刻。聽到一個新的觀念,那種幸福的感覺是很難想像的。
我除了教研究生以外,還教了一些小學生和國中生,這些比較不幸的孩子,多半都表現得很好,好幾位都已經大學畢業,可是也有幾位使我牽腸掛肚,每天為他們擔憂,因為他們都沒有唸高中,只有國中畢業,能找到什麼工作呢?我常常希望有朝一日,我做了政府大官,一定要設立一個機構,專門幫助中輟生,使他們長大以後,能夠多一點競爭力。
可惜,我不是大官,因此只好眼看我的學生變成了中輟生,雖然我仍願意教他們英文和數學,卻常常找不到他們,不知道他們到哪裡去了。對於我教過的研究生,我期望他們在事業上非常地成功,但對於這批中輟生,我唯一的希望是他們沒有變壞,只要他們沒有變壞,我就心滿意足了。
人總要老的,再過幾年,我就七十歲了,奇怪的是:我仍希望我能再活三十年,如果我真的能再活三十年,我仍要壓迫我的研究生和我一齊做學問,我相信我們能設計出更好的線路,發展出更好的分散式系統,也能設計出新的演算法。我更希望我的學生不要成為中輟生,即使他們中輟了,也不要變壞,而且願意讓我這個老頭子繼續地教他們英文和數學。
我最遺憾的事是我在這過去的這三十年內,一直住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裡,那些研究生可以說是天之驕子,他們的前途非常光明,他們的下一代也是如此。可是我教的另一批不幸的孩子呢?我就完全沒有把握了。